
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中文版8月起停刊。看到消息,心中无限感慨,因为我和读者文摘有段长而深的因缘。
读者文摘版本很多,最早创立的是1922年英文版,创办人是美国的华勒斯(De Witt Wallace)。中文版始自1965年,首任总编辑是林语堂女儿林太乙女士。人们说她是读者文摘中文版创办人,也有道理,因为读者文摘中文版在林太乙手中问世,发扬光大。
注重人文尊重宗教
林太乙与我岳母林海音女士是好友,我得以见面。她拿着刚流行的Palaroid相机(商业名称拍立得)在客厅拍照片,几秒钟后照片自相机中滚出来,光彩艳丽,她签名,我很珍惜。几十年后照片褪色,影像消失,变成一张发光的灰纸。
香港编排的「读者文摘」中文版是我固定读的两本杂志之一,另一本是台湾高雄炼油厂编的「拾穗」。那年代杂志很多,这两本是文摘性质,不刊载儿女情长的小说,也不谈耸动的政治。拾穗着重科技,读者文摘着重人文。但读者文摘有个不明说的精神,「我相信你知道,读者文摘选取的文章注重人伦,尊重宗教。此外,我们很反共,但是不在辞句上鼓吹,尽量选用富含自由、人本、家庭、快乐、幽默本质的文章。」1995年远东区美籍总经理在他香港办公室,曾私下对我这么说。
聘专人严谨查证
读者文摘对文本的要求极为严格,不能有错别字,讲究文句优美,不能模棱两可。他们设立了对外不公开的审核机制,聘社会人士考证转载文章内容。作者往往是名人,但文句未必妥当,读者文摘不方便直接询问,借资料查证员(researcher)考证,若有必要请求作者更改。1970年代,林太乙商请夏祖丽担任考证,希望我协助。当时夏是纯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我负责电视新闻主编。他们曾希望转载一篇散文名家的文章,文中提到「…北一女是台湾数一数二的好学校…」,读者文摘要求证实「数一数二」是否恰当,祖丽把考证任务交给我。
查证员宛如FBI探员
我先到教育部,请求调阅近年台湾各中学毕业生,联考升大学达成意愿的比例,再查看各校学生违犯校规的情况,以及体育、群育、校外活动、社会评语等,总结是「数一数二」这形容词很恰当。否则也许会建议,由读者文摘请求作者改为「北一女是台湾很好的学校」,或「人们趋之若鹜的学校」等。
读者文摘想转载一位名家写的游记,文中说,「…台湾的外销三轮车驰名国际…」他们质疑这句话,祖丽交付我考查。三轮车在台湾早已绝迹,我到国贸局查看出口货物分类,没有三轮车,只有自行车,台湾省和台北市进出口公会也一样。有人建议去罗斯福路一家自行车行,原来他们把链条、把手、车轮、车架分别卖出国,在夏威夷组装成三轮车,在缝纫行缝制美丽的车篷、椅垫和「台湾制」字样,由老美骑了在檀香山街上兜揽观光客,难怪这位作家见了说,「…台湾的外销三轮车驰名国际…」。
林太乙说,「我们除了太阳从东方升起不用考证,其他描述都要考证。」我知道除了祖丽,读者文摘另有位兼任的researcher,也出自新闻界,大家都不宣扬自己,好像是CIA或FBI探员。
创建题库统一翻译
1986年我辞去华视,应聘澳洲联邦媒体担任新闻主编,我们与读者文摘那份「暧昧」关系告一段落,仍偶然为其写稿。1992年读者文摘总编辑郑健娜女士找我兼任每期文章的英翻中工作,一连做了九年。我深知他们的规矩,翻译成中文常加注出版时不会看见的理由。读者文摘的全球各种语言文章一律翻译成英文,储藏在大电脑中备用。他们称作reservoir(题库)。
1994年尾一个早晨,还没起床,一名不认识的女性打电话到床头,以英语对我率直说,介绍我改行到香港工作,薪水比现在高一倍半。她悉数我过去在台湾和澳洲的工作细节。我问她是谁,如何知道我的电话和个人数据,并表明我不想转换跑道。原来她是受雇的合法headhunter(猎人头顾问),专替雇主寻找或调查他们看中的人的底细,类似星探或球探。她要求我去香港与雇主面谈三天,来回商务舱机票以及在香港的交通食宿都由对方负责。我坚持要知道雇主身份,否则不去面谈,她才说读者文摘找继任的编辑负责人,看中我。其实我已猜到,因为常年与读者文摘工作双方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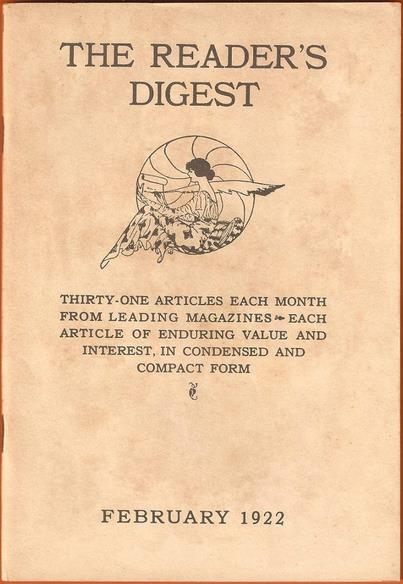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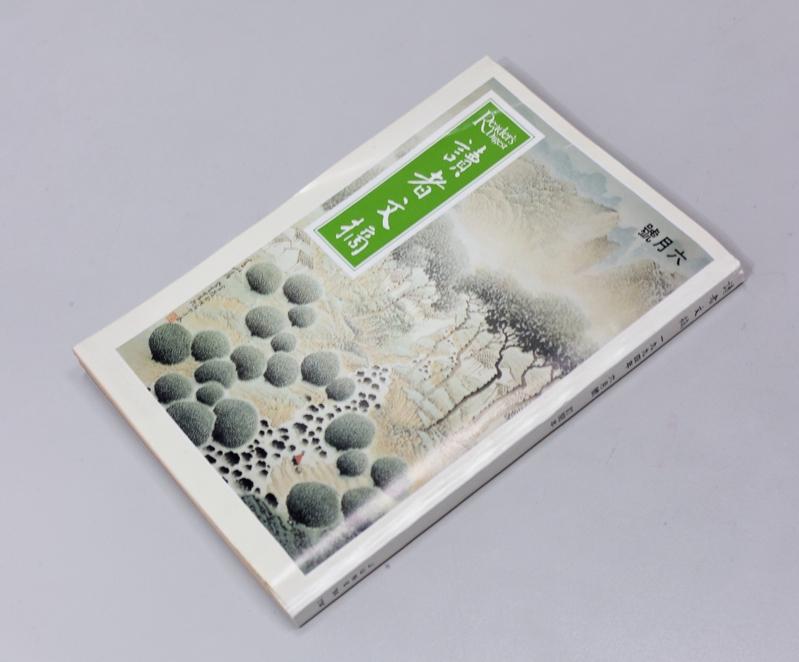
一场私下高薪挖角
飞机上我审视一切,我曾被访谈,也常访谈别人。当时读者文摘有18种语言版本,包括盲人点字和有声录音。最畅销的是英语版,其次是中文版,各版本必须翻译成英语备用。纽约总部每期规定不同语言版本必须刊载的文章,各语言版也可自行选取文章,或从外界转载,或自行约定撰写。中文版刊载的题库文章和自行选用的文章比例,约为7与3。
我身着便装抵达香港,一身黑色礼服的司机,打开奔驰车后座门说,「这是你今后三天的专车,我是你的司机,要到哪里请吩咐。」我问现在去哪儿,他说香港中环太古金钟广场,新开幕的万豪酒店(Marriott)。休息片刻后,去柴湾的读者文摘。
接任总编辑的机会
在那名美国远东区总经理的办公室,他说了大篇读者文摘的理念后告诉我,「我们希望你先担任一年的主编,现任总编辑郑健娜明年退休后,请你接任总编辑,十年后退休。」他说,退休时按最后的薪资,支付三年半做为退休金。另外每年支付全家四口各四张香港墨尔本的来回商务舱机票,做为home leave(探亲假),机票可换成世界任何地区,不能折现。他敲敲办公桌底层,「这是我和你的under table(私下协商)」。他乐观地希望三天内签约。
我颇奇怪,首度见面就谈台面下交易。他对我的「好感」依靠的是总编辑等人对我的了解,以及那名head hunter的调查报告。他好像在谈商业交易,不是发掘新激活人员的价值。我联想到他所说的读者文摘精神。
「谢谢你提供的优厚待遇,即使我正在享受澳洲联邦政府的安稳工作和待遇。我想知道,转换读者文摘工作,对个人会有不便吗?」,他想了想后说,「你必须习惯搭飞机,每年两次由香港飞纽约开会,检讨编辑发行,配偶可以同行,会安排活动。每次公假只有一周,扣除旅途往返和开会,所余时间有限,但是我们有18洞的高球场。」他说,「你还必须每年至少一次考察各市场。以中文版来说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尼。你一年还有四次家庭团聚,所以你会全年不停飞行。当然你要负责每期文章,指导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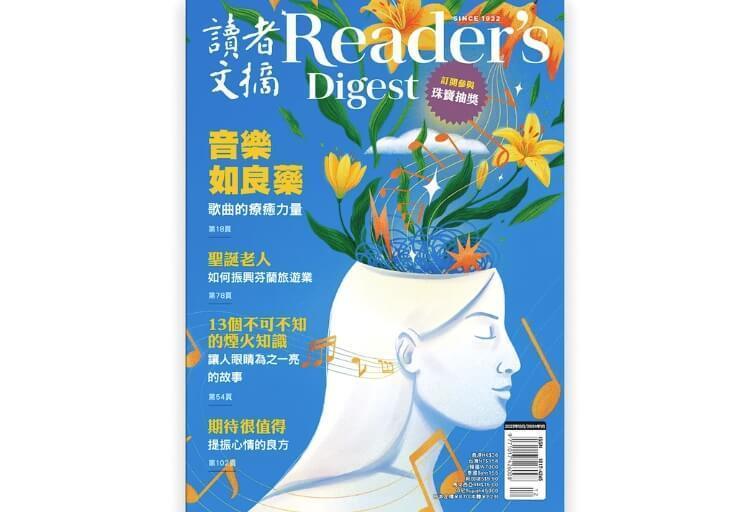
他反问我,读者文摘选择我的原因是什么。「我猜是考虑中文版无法打入华人最多地区的中国大陆,因为中共不准。而我对两岸和简体字都很熟悉,出身和经历符合你们需求。」他却说,「我们不考虑中国市场。」我问,「你们担忧1997香港回归后的读者文摘情势吗?」他说,「不担心。中共不敢赶走读者文摘。」当时读者文摘与时代杂志(Time)、生活(Life),合称美国三大杂志,读者文摘的国际影响力很大。他却没料到13年后的2008年起,读者文摘以简体字在中国销售了四年。
香港或澳洲的抉择
在香港的三天,我忙于了解编辑部运作。第一天傍晚7时30分我搭电梯下楼回旅馆,一名编辑小姐有礼貌地问候我,我随口问,「妳们平日何时下班?」她说都是这个时候,我问,「有加班费吗?」她噗哧一笑,摇头。我立刻醒悟自己的愚蠢,我这人在澳洲工作惯了,没考虑到东西文化的工作差异。
我邀请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梁教授、联合报驻香港特派员俞渊若女士,分别餐叙,听取他们对我就任新职的意见。一位肯定地说,「当然该来,除了待遇优厚外,工作地位崇高,你是继林太乙、董桥、郑建娜之后第四人。」他指着酒店说,「香港多繁华,如果有天堂就是这样子。」另一位说,「如果我是你,不来。看看1997之前,有多少人急着离开香港?你却一头栽进来,撂下祖丽一人在澳洲带读书的孩子。澳洲是香港人向往的地方,你没有理由放弃。」
为家庭婉拒职缺
回到墨尔本,我与祖丽悉心检讨。她的意见是3:7,不去香港。理由是,人生的下半段单身在香港食宿,工作辛苦,划不来。我的意见是6:4,去香港,理由是人生另一冲刺,待遇好,能发挥所长。不去理由与祖丽相同,抛家弃子,形同打光棍。于是,9:11,我们下定决心婉拒那总经理。
于是我回复:「你们的待遇令人满意,可是我好像没得到全部,因为必须负担澳洲香港两边家计。我要在居住昂贵的香港租屋,要高级安宁、有警卫和雇佣,要步行可达读者文摘,这一是为工作方便。除非这些问题能解决,否则恕我不能就任。而这些问题属个人困难,不该由读者文摘解决。」
还没接到回信,我接到澳洲电信局Telecom的通知,要我去墨尔本电信局总部参加一个越洋卫星视频会议(satellite video conference),30年前这东西刚激活。对方是纽约的读者文摘总部总编辑,国际版总编辑,与人事部门经理。他们在银幕上三对一,冀求我回心转意。
东西文化交融价值
两年后,1997年我们在墨尔本亚伯特湖(Albert lake)湖畔Carlton Crest酒店,主办三天的「中华文化与移民文化国际研讨会」,邀请三十几位国际学者和文化工作者共同讨论文化跨越问题。我是大会主席,祖丽负责议事,机票和食宿完全由我们负担,就像前年我去读者文摘。我邀请郑健娜来墨尔本,她的讲题是「跨越一道文本的鸿沟(Bridging the Chasm between Languages)」,当天她提到「…不同文化的创作者,历练不同,看法不同,表现手法各异,但我深信人性有许多地方是共通的,譬如对家庭、感情的追求,对信仰、价值的探索,对未来的憧憬等。凡此种种,不同种族、肤色、语文,都深深向往。从文化消息方向看,中西文化的确可以交融。…」郑健娜不是演讲读者文摘,但是内容却契合她的工作。
在我和读者文摘的多年合作中,深刻体认她说的东西文化交融价值,因为读者文摘设立题库,把千万篇世界语文精华,一体用英文储藏,供各地编辑倘佯,编排成书,供千万读者浏览激励人心的好文章,乃至小品专栏,像「开怀篇」、「浮世绘」、「世说新语」、「医学新知」,以及连载的「老周的身体」。
读者文摘鼓励世人,为人生奋斗,却在60寿诞时停刊,情何以堪。2025/7/27 台湾淡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