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经济上半年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展现了韧性,但下半年专家普遍不看好。基尔世经所研究员刘宛鑫接受DW记者访问,提到中国经济放缓的可能,以及扩大内需的困难。她也分析,欧洲多数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彻底警醒,并建议应该透过谈判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过度补贴政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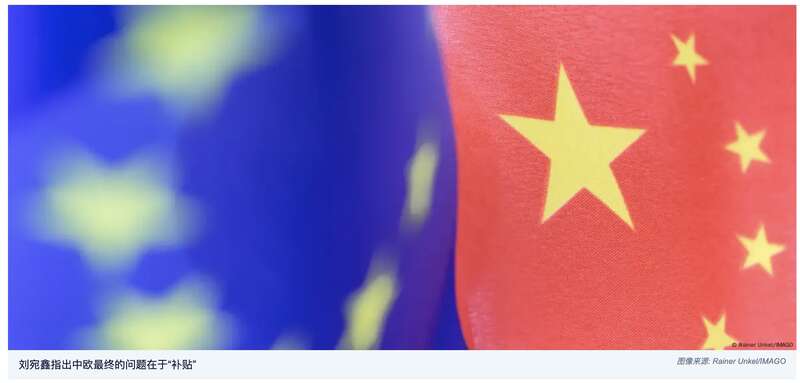
DW:中国最近的经济表现不错,尤其是对外出口强劲,中国挺过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了吗?刘宛鑫:到目前为止不能说中国挺过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因为这个贸易战还是持续在进行。中国现在的出口整体表现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要提高关税,而中国的企业一直以来的反应都很快,因为预期会有比较高的关税,所以提早把很大一部分的产品出口到美国,避免高关税。所以我们看到上半年出口是比预期好的,包括第一季度增加其直接出口到美国,上半年增加其出口到其他国家比如东南亚,而这其中很多商品最终是要销往美国。出口支援了中国第一跟第二季度的经济成长,但这不代表今年度它的经济成长就会完全没受到贸易战影响。还有一个原因是双方只是暂时性休兵,即使在瑞士与伦敦两次中美会谈后双方发出正向的信号,但不代表可以达到最终的会谈目标,中国现在跟美国贸易战还在持续进行中,90天之后,8月会发生什么事情亦或是政策的走向没有人知道,因为特朗普的政策不确定性非常高,只要双方再有冲突点,特朗普的回应很可能就是再提高关税,到时中国将如何反应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除了中美双边之间直接的贸易战之外,中国现在在全球经济和贸易里面扮演一个非常中心的角色,美国又持续跟其它的国家有贸易战,想要对欧盟的商品加征30%的关税,也对于越南和巴西等其它国家加征关税,中国一定间接地也会受到影响,所以现在讲中国是不是已经挺过美国发起的贸易战还太早。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刘宛鑫博士接受DW专访图像来源: DWDW:在接下来下半年或明年会看到中国经济放缓吗?
刘宛鑫:如果去看中国的经济成长目标,以官方的资料来看,就2006年到2024年的经济成长来说,除新冠期间官方的经济成长率永远都是高于经济成长目标,似乎一直以来都可以达到目标,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去年还是有5%,为什么会大家说经济情况不好?为什么人民也感受到经济发展的情况并不是那么好?
其一就是中国官方经济资料的可信赖度在哪里,这是一个问号。即便说我们不讲说政府可能对资料上面有一些操纵的可能性,在经济政策上,它有很大的空间可以透过推进经济政策去达到想要有的经济成长率。所以你会感觉到说经济成长率资料还是很漂亮的。
至于今年会不会放缓,现在等于是说第一、二季出口支撑了很大一部分的经济成长,可是你不可能无限制的出口,因为国外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不可能无限。上半年中国企业先增加出口避关税,但这个产品它可能是大量存在仓库里面,这些东西要先卖掉之后才有可能从中国再度进口这些商品。假设美国之后真的又提高关税、外国需求降低,即便中国有产品可以出口,需求低的情况下也不会再出口这么多出去,所以中国的出口刺激经济成长这块动能就会下行。
放缓是非常可能的,在第三或第四季度,只是说第三季度我们会先看到一个放缓。可是如果看中国以前的季度发展,基本上第三季度就是成长率会下来,然后它就会在9月底、10月初的黄金週之前,出台一些政策刺激经济成长;第四季度再上来,达到全年的经济成长目标。
现在就要看第三季度会放缓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可能现在刺激内需的政策有办法让放缓不那么严重,小部分的吸收可能没办法出口的这些商品,维持经济成长在一定的程度,但是这个的成效是多少有待观察。基本上因为上半年的经济发展比预期好加上中国政府有一定的能力去刺激经济成长,所以下半年的经济不至于放缓太多。
DW:中国要扩大内需的困难点是什么?
刘宛鑫:扩大内需并不只是2012和2013开始讲,其实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开始讲,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开始有经济放缓的趋势,市场需求包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下降。中国发现以前都是靠出口,现在如果西方国家比较少买我的商品,中国必须要靠自己的市场去吸收这些商品,所以它其实从2008年就讲要扩大内需,只是中国也讲了很多其它的发展目标,当初扩大内需只是很多目标的其中一个,现在是更强调了。
另外一个差异在于,2008年之后的扩大内需强调的是,透过比方说政府的投资,或者是鼓励企业的投资,去吸收产能过剩的商品,例如建筑材料,或者是透过2012年的一带一路扩展到其它的可能的新兴市场,把这些产能过剩的产品卖过去。当初扩大内需的一部分是增加出口市场的一部分去处理产能过剩问题。这样子会导致什么问题?有一些企业虽然说购买了建筑材料,比如说房地产业,房地产业的快速扩张与发展导致后来一些包括说债务的问题等,其它像是绿色产业如太阳能板与新能源汽车等,大幅鼓励投资之后产能过剩了,那只是把产能过剩的问题从上游转移到了下游,但这些产品最后要出去哪里,这个问题到现在更加的突出。
一直以来,这些产品有一部分内需,有一部分也是外销,那这个问题现在就会越来越严重,因为西方国家开始担心,比方说中国补助新能源汽车,影响到市场的公平竞争,它要减少或阻止这些收到政府很多补贴的中国产品出口到这些国家。所以中国现在更加要去强调内需,而且是消费者的需求,而不是企业跟政府透过投资去增加内需。
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消费者要去买你的这些产品?我们先假设消费者是有购买力去买这些产品,可是他们真的去买吗?因为你看到新能源汽车的产能是增速是非常快的,消费者不可能每年换一辆车, 即使有那个能力或意愿去买也不可能。又比方说太阳能板,房子做太阳能板不会是短时间就去换新的,可是企业的过去几年扩大的产能一直在这里,每年可以生产这么多,即便说中国政府有政策去刺激,让消费者可以去换新产品,可是消费者不可能每一年去换这些耐久品。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消费者比较愿意去存钱,为什么?很大原因是,以前经济发展情况还满好的情况下,消费者就很愿意存钱了,因为社会保险福利制度不完善,民众会觉得说,我必须要有那个钱存在那里,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才有那个钱可以去处理新的问题,包括医疗保险,所以它会把钱存下来,不去消费。但现在担心更多是未来的前景,担心之后没工作,经济发展情况是更加放缓的,公司赚不了钱,员工虽然保住工作但必须要自动减薪,又或者是其它的赚钱渠道风险提高,包括会担心如果证券和金融市场发生一些问题,会损失更多的钱,所以要更加的小心,更加的不愿意花钱,而是存钱。那怎么去刺激内需?
最后就是,中国有通货紧缩的问题,物价指数趋势是下来的,如果预期通货紧缩,预期价格会再下来。消费者会去想说,预期价格会下来,为什么我现在要去买?那我就宁可再等。这个问题很大,因为如果继续再等,就没有人去买,就必须要靠政策去刺激。政府说,你现在去买我给你补助,即使说未来价格还会再下降,可是你不会损失那么大,你现在就去买就可以,但如果消费者还是不买单,厂商没办法卖产品,运营上就会有困难,就必须要开除人力,整个经济情势就更惨、更往下滑,消费者就更担心会受到影响,就更不愿意消费了。所以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
要提振内需最大一个重点就是怎么要提振消费者信心,不能只靠以旧换新政策,这样不够。要提振消费者信心、而且也要提振企业的信心。因为虽然说消费者可以买最终产品,企业还是必须要愿意去投资,才可以继续刺激内需,可是这两部分现在都是不容易做到的。
DW:回头看过去10年,您觉得“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成功的产业政策吗?
刘宛鑫: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很多,所以要分开来看。可是我先讲一个并不是它表列的目标,中国制造2025及其相关政策表明产业想要达到先进制造到哪个程度,这提高了西方国家对于中国企业与产品的警觉性,对于中国的野心、发展的方向和愿景有一定程度的警觉。
在中国制造之前,甚至之后一、两年,欧洲很多人都还是觉得中国是一个生产低科技、高人工密集产品的国家,很多人没有去想到,中国其实生产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密集的产品,即便说它并不是处理所有的技术,可是并不是像以前只是生产衣服、玩具,它现在可以做越来越多科技密集的商品如成熟制程芯片与其他电子产品等,在欧美很多人忽略了中国其实在制造业是在往高科技发展且逐步推进的。但是中国制造2025年就很明确跟你讲,我要发展到这个点,所以西方国家就开始担心,去警觉到说我们应该也要做点什么事情,去正视中国的崛起,作为一个可能对于产业竞争上的威胁。
在此之后,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跟欧盟开始努力更加积极地思考产业政策要怎么做。不然以前,尤其在德国,没有所谓的产业政策,最多就是去补助研究与开发,它给企业很多空间去决定要怎么发展,可是中国制造2025让它们仔细去想要怎么样建构产业,怎么去应对其它国家。
DW:虽然中国十年前就说了,但现在看来,中国在很多领域已经是领先了,欧洲就是落后。
刘宛鑫:欧洲就是一直在讨论,这就是问题,在德国和欧盟会讨论很久才会达到一个共识,会有一个政策出来,可是要达到共识做决定要花很久的时间。老实讲,即便欧洲很早开始正视这个中国带来对欧洲产业的可能挑战,大家还是看到企业是赚钱的,外企在中国很长时间是赚钱的,没有很大程度会去担心中国对我的安全有任何的威胁,而是觉得说这就是全球贸易和交流,大家都有赚钱,这是一个对大家都好的事情。现在要进一步去看中国对于经济安全,对于整个安全大方向和技术的自主性会不会造成什么的威胁,也就拖到现在才更加的进一步的去思考讨论政策应对方向。过去十年虽然说开始去思考,可是没有真的做什么事情。
DW:所以北京成功了?
刘宛鑫:以“中国制造2025”本身的目的来看,第一个重点是降低对进口的依赖、对外企的依赖, 这个是成功的。虽然还是有一些产业还是必须要依赖进口、依赖外企,但比例是下降的。尤其是在新冠之后,进口是下来的,当然进口下来不等于是减少对外企的依赖,因为有一大部分是要求外企进中国、本土化。但是外企本土化的同时,有很多的中国企业是起来的。有些德国的企业因为新冠期间没办法派工程师去处理机器的问题,给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机器抢进市场发展的可能性,所以第二个目标,降低对外企的依赖,也有达到一定的成功。第三个目标是要提高竞争力,这个是有一部分程度达到的,即便当中也是有很多资源配置低效率与市场失调与扭曲的问题。
DW:现在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已经外溢到欧洲来,有关国家如何应对?
刘宛鑫:欧洲不能一概而论的原因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产业受到的冲击会不一样。产能外溢的问题,比方讲新能源汽车,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获得的补助,造成对市场公平竞争的威胁,这是一个贸易的议题,贸易的议题就是欧盟的议题,不是各个国家本身的议题了,而是以欧盟的角度去处理。如果是因为补助导致产能过剩,导致影响到公平竞争,欧盟有工具去应对。所以去年有一个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调查,结果就是要求要提高所谓的反补贴关税(countervailing duty),这并不是报复性关税,而是应对因为中国政府补助给带给中国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很多人直接把它翻成“报复性关税”是错误的,欧洲就是透过这个关税去降低补助对于产业的冲击。虽然加征了这个关税,但是欧中双边还在沟通,看能否达成其他共识如提高中国汽车在欧洲的售价亦或是中企在欧投资,来替代加征这反补贴关税。
但中欧新能源汽车贸易最终的问题在中国对其的补贴,如果只是去透过关税或是提高售价去弥补价差,无法解决补贴造成的问题,这其实没有意义。因为补贴还在的话,加上中国的企业发展到现在,竞争优势是在的,是有降低成本的空间的,只要持续的发展,它可以继续降低它本身的产品的价格,即便加征关税,价格还是低。对于中长期来看,没有真的处理到补贴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建议是,欧盟要利用关税这个工具去跟中国政府谈,最终的问题是补贴。中国的企业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就不需要再补贴它了,它其实是可以跟其它国家竞争的,这是可以要求中国去做的。
中国这些企业因为产能过剩可能导致欧洲企业遇到的一些威胁,很多人就讲说,那我们是不是要保护我们欧洲的市场,是不是应该要开始在政策上面支援欧洲的企业,让它们更有竞争力等等。甚至有些人开始讲我们是不是也要补贴,可是这个方法其实不是最有效,也不是说对于资源利用有效率的一个方法,因为政府补贴就是会影响到市场公平与竞争。
欧洲不能只是拷贝中国的产业政策,而是要持续研发创新以提高企业本身技术和产品的质量的竞争力。如果只是补贴性的竞争,最后就是谁有钱谁赢,中国是有能力继续再提高补贴,这样子补贴性竞争,最终大家都是输家。
很多人就说,是不是有一些其它的贸易防御工具,把欧洲市场留给欧洲企业,但这也不是一个好方法。这样保护欧洲市场没有意义,因为这个市场即便大还是有局限性,欧洲的企业的产品最终还是必须要卖到国外去,如果保护的只有这个市场,怎么去跟国外还是跟中国企业竞争,中国的补贴问题还在的话,欧洲没有办法去竞争,反而还会加剧欧洲企业在国外跟中国的竞争,因为当中国企业的产品没办法卖到欧洲的话,就要卖到更多其它的国家,可能更加压低它的产品价格,欧洲不可能这样跟它竞争。
DW:北京有什么理由停止补贴?
刘宛鑫:中国的补贴并不是只有正面效果,也导致了很多的问题。虽然真的有一小部分的企业获益,但是谁说政府最能知道未来发展的方向,这个资源投注在别的方向搞不好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功,因此中国资源投注是否有效率是受到很大的质疑的。 比方说新能源汽车,根据我们去年的报告,因为补贴政策中国现在有很多的新能源汽车公司,但最终不可能所有企业都可以活下来,最终会变成内部有一个很大的竞争,大的企业有更多资源的企业会留下来,小的就没有,投注在这些企业的整个资源,生产过剩的这些新能源汽车,这些资源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这些成本是在的。
西方国家现在看到只是中国的成功,没有看到失败的点,比方说它补贴其它的一些产业,像是半导体业,没有达到目的,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补贴都是成功的。还有因为它的资源是集中在补贴某些产业,没有用在比方说改善社保,提高医疗保险,或是教育方面这些的可能性,只投注在产业政策,这样的资源配置对社会整体来看是有问题的。另外,没有投注在社保,大家就更加的想要存钱,消费者不愿意买东西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资源的投注是没有效率的,导致的是部分产业产能过剩,消费者又不愿意买的情况下,还是必须要出口,但因为补贴导致公平竞争受到冲击,增加跟其它国家的紧张关系,所以西方的一些国家就开始反制,最后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还在那里。
最终中国会面臨到,怎么样去处理内部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也因此为什么欧盟主席说中国必须要处理自己内部经济的问题,不能够把内部经济问题外溢到其它国家,让其它国家去帮它解决。以前解决产能过剩方法很简单,可以把商品卖出去,别人去买,就不需要去解决内部的问题,可是现在其它国家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了,中国就会被迫去正视自己的问题。
DW:台湾在这中间扮演什么角色?
刘宛鑫: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疑虑加深,对于它们自己本身的经济安全顾虑加深,就算完全不考虑台湾,比方说美国的政策,某些产品不能出口到中国,或者是欧盟针对新能源汽车的调查、加征关税,现在也有对于中国的风力设备厂投资欧洲的一些调查,还有其它的贸易防御机制工具使用,这些都会让中欧或中美的紧张关系升温,反而维持跟台湾之间的贸易关系,政策跟经济的成本没有像以前那么高。 欧洲过去也曾有讨论是否也该减少对台湾经济依赖以降低两岸冲突倒置的风险。但世界上的AI芯片毕竟90%来自台湾,台湾本身有它自己的优势,不那么容易的成为大家多元分散政策下放弃的市场。
以前如果只是为了维护跟台湾的经济关系,不让台湾对中国的依赖加深而去支援台湾,而有一些防御的政策的话,可能会遭受到中国的反击政策,但现在反正在做了,这个成本是降低的。那个差别是,欧洲现在本身就是为自己的利益而考量,不是为台湾的利益考量,所以它对于台湾来讲是一个有益的发展方向,等于是间接从中获利。大家会发现,基本上还是需要台湾,又加上现在辉达要在台北投资AI芯片、超级电脑和机器人。现在的方向就是,欧洲不会刻意去提支援台湾,因为提这点对欧盟没有意义、对台湾没有意义,默默地做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