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追求高等教育,往往意味着生活中将迎来许多变化: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学术挑战以及个人成长的机会。如今,17至20岁进入大学或学院的学生,还要面对重大的压力:经济负担、心理健康问题,以及不断变化的人工智能与虚拟课堂体验。
对家长来说,如今的大学生活与他们当年的经历已经截然不同。于是,《环球邮报》的记者Daniel Reale-Chin直接问了学生:现代大学生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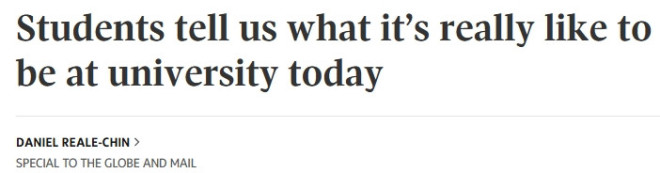

Jessica Qian: “我花了很多时间独处”
在被UBC大学录取后,Jessica Qian 选择住在卑诗省三角洲市的家中,每天通勤去学校。主要原因是她要照顾三岁半的小狗Charlotte,在她攻读动物生物学学士学位时,这只狗给了她很多安慰。
大学一年级的真实感受:
很有意思。我之前念的是宗教女子学校,上大学对我来说简直是颠覆性的体验。高中有很多限制,而大学里,你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这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不同性别、身份和文化的人,眼界被打开了。
大学里最大的变化:
是独立性。高中时,小团体很多,你常常找到一个朋友圈,然后一直待在一起。大一时我在校园花了很多时间独处——找教室、空档时间安排做什么,以及约好时间和新朋友见面。尤其是像我这样走读的学生,没有宿舍可以回去,很多时候只能一个人在校园边吃午餐边学习。

我通过UBC一个为同届新生设立的Instagram页面认识了两个朋友:一个是来自迪拜的国际学生,另一个和我一样想读兽医学院。我们经常约着去逛商场、尝新奶茶店,或者只是闲聊。
希望父母当时能告诉我的建议:
父母没有让我做好交朋友的心理准备,也没告诉我交朋友有多重要。我不怪他们不了解,但我确实希望当时能得到一些维持友谊的建议,或者被鼓励去参加更多社团、多认识一些人。
Helena Zhu: “我希望自己能多花时间享受生活”
Helena Zhu就读于金斯顿的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健康科学专业,志向远大——希望将来进入医学院,成为一名麻醉科医生。
住在校园的真实感受:
我很幸运在宿舍里有一间舒适的单人房,只需要和一个人共用浴室。我们四楼的公共活动室是大家聚会、学习、交朋友的地方。刚开始我非常想家。大学里心理健康问题非常普遍,我认识的几乎每个人都在挣扎,因为大一的过渡真的很难。宿舍的同学成了我很重要的支持系统,因为我们都在经历相似的挑战。

父母给对了的建议:
我父亲教我无论何时都要有目标,并制定达成目标的计划。这让我有了方向感,也让我学会了为自己争取,比如在找助教谈成绩时,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得到某个分数,或者在听不懂某个概念时要求额外辅导。
父母给错的建议:
他们让我参加很多社团和课外活动。结果我大一加入了五六个,其中一个叫“Swimming With a Mission”,教社区有残障的儿童游泳。但这么多社团让我分身乏术。如果可以回到大一,我会放慢脚步,更多地享受生活。与其急着什么都去试、害怕错过,不如留些时间慢慢体会。
Dominic Lora: “也许如果我住在校园,经历会不同”
高中毕业后,Dominic Lora曾收到达尔豪斯大学、圭尔夫大学和康考迪亚大学的录取通知,但他决定先间隔两年。他通过在夏令营打工、帮父亲(电工)干活、维护游泳池等工作攒下钱,和最好的朋友Ollie一起去了肯尼亚四个月。现在,他刚刚完成在蒙特利尔康考迪亚大学的大一课程。
间隔年教会我的大学经验:
在肯尼亚,我们在孤儿院工作、执教篮球队、参加音乐节,还沿海岸旅行。在孤儿院的工作让我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住青年旅社时,我们结识了很多来自英国的同龄人——在那里,“Gap Year”是文化的一部分,这也让我更坚定地觉得我做的是对的。
回到多伦多后,发现自己的人生节奏和一起长大的朋友不一样,这种落差让我对大学生活有些消极,即便入学本身是令人兴奋的。
父母给对了的建议:
我很庆幸父母让我提前为独立生活做准备——自己租房、交房租、洗碗、倒垃圾、学会当好室友、在学业与生活之间找到平衡。他们教我,无论好坏,都要珍惜经历,并且大学生活并不容易,需要应对教授的各种要求。
大一的真实感受:
因为我比同龄人晚两年上大学,所以觉得和小两岁的学生一起住校园不太合适,于是我和Ollie在蒙特利尔租了公寓,骑城市单车通勤上课。
我原本以为大学是一个总在外面社交、结交朋友、建立社群的地方,但事实并非如此。学生压力很大,我总觉得自己必须维持一个“形象”。我不敢一个人去酒吧或派对。在蒙特利尔,我甚至比在肯尼亚还要感到不自在。
我记得放寒假和学年结束时,自己非常开心能回家。有很多次,我都不想去上课、不想继续留在蒙特利尔、不想和校友去打篮球,但我还是逼自己去做这些事。事后我很庆幸,即使在状态最糟的时候,我也坚持做了。
也许,如果我住在校园里,我的大学生活会完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