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已成“外卖之城”——且此趋势已无法逆转。
堂食空间不断缩小,“纯外卖”品牌迅速崛起。餐馆老板一边无奈迎合市场,一边感叹利润被吞噬殆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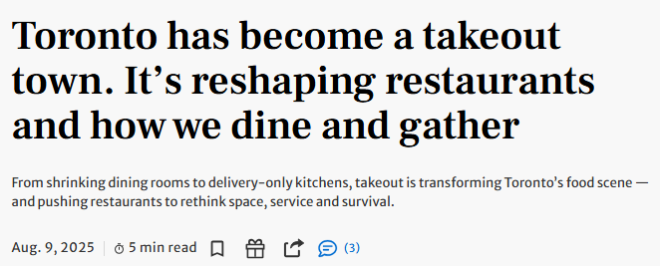
厨房“一分为二”做外卖
在West Queen West的Curryish Tavern餐厅,主厨兼老板Miheer Shete把厨房硬生生一分为二:一边是维系口碑的创意堂食体验,另一边则是今年春天新推出的纯外卖品牌Jhakaas,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我们的食物在餐厅里吃才是最佳体验,”Shete说。但去年堂食预订下滑,他只能用相同食材、同一厨房,做出低价外卖菜单,让员工有活干——哪怕座位空着。
“开业第一年,我们完全没想过用Uber Eats。我不需要它,我希望客人都能亲自来店里。”
讽刺的是,Curryish本来就是疫情期间从外卖起家。如今,外卖又反过来吞噬了堂食。

Shete的故事并非个例。餐厅不再追求“氛围”,而是围着外卖平台转——座位减少,员工一人多岗,店里除了交谈声,还多了App提示音和外卖员的取餐报号。
随着外卖和配送的扩张,一些人开始担忧,餐厅的社交功能是否正开始瓦解。
座位都去哪儿了?
如今缩小或取消堂食区的原因,不再是公共卫生限制,而是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
加拿大餐饮业协会(Restaurants Canada)首席执行官Kelly Higgleson表示,很多餐厅老板正主动缩小店面规模。“尤其是在房租不断上涨的大城市,我们听到超过一半的经营者表示想减少面积,因为空间成本高,而第三方外卖平台又在快速发展。”
住在奥辛顿(Ossington)一带的38岁教育工作者Naomi Perley也注意到了变化。她常常得去附近公园找野餐桌吃午餐。“感觉有些餐厅就是默认你要么回家吃,要么在车里吃。”她说,“冬天怎么办呢?我真希望那些以外卖为主的店能多放几张桌子,但我猜他们不想麻烦,也不想提供堂食服务。不过,这多少有点不够友好。”
在肯辛顿市场(Kensington Market),Good Egg的老板Mika Bareket见证了她自1980年代以来一直居住的社区,从一个遍布小型杂货店的地方,变成了一条充斥着外卖店的街区。她说,许多狭窄的店面本就不是为室内用餐设计的,所以顾客只能挤在人行道和路边,把垃圾桶当作临时餐桌。
“现在这个社区主要都是游客了,他们常问我们哪儿有桌子。”Bareket说。

外卖能赚钱吗?老板说:很难
当然,餐厅老板们都希望看到座无虚席的餐厅,但随着外卖的普及,他们觉得自己不能忽视这个市场。
“很多时候,我们得搞买一送一、送可乐、送薄饼。”经营The Host连锁印度餐厅的Ashish Sethi说,“如果不做促销,你就不会出现在搜索结果的前列。我们还算有点名气,但想吸引新客,没有优惠几乎不可能。”

Sethi估计,现在外卖占他生意的30%-40%,是疫情前的两倍,但利润并没增加。一份20加元的黄油鸡,如果顾客直接向餐厅点单能净赚4-5加元,经外卖平台抽成后不到2加元。
“说实话,这不是什么赚钱的生意。”他说,“只是为了维持出品量,保证能达到供应商的最低起订量。”
Jhakaas的Shete也同意这一说法:“我们第一周没有做买一送一,一天就一两单;然后我们加了优惠,一天15单,其中12单是买一送一。到头来,我每卖一个10加元的汉堡,只赚1加元。”尽管如此,他说曝光度仍然很重要,打折单有时会带来后续的餐饮或团体订单。
士嘉堡经营尼日利亚餐厅Blessinglicious的老板Blessing A.在社交媒体上毫不避讳地分享经营的喜与忧——她的餐厅大约80%的订单来自外卖。

她曾晒出一张12月的DoorDash销售截图:销售额10,200加元,平台抽走4,300加元佣金(外加税费),另外还有260加元因订单争议被扣除,实际到手约5,300加元。那些争议款项有时甚至会导致她要为某些订单倒贴钱。
“那些钱本可以用在餐厅里。”她说,并告诉顾客最好直接向餐厅下单。“半年付给外卖平台的佣金,都够我们买一辆车,再雇人自己送外卖了。”
待客之道正在消失
餐厅顾问、美食作家Corey Mintz发现,一些较新的餐厅——尤其是疫情前没有堂食基础的——如今对待堂食服务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他回忆说,最近点了一份沙威玛(shawarma)打算在店里吃,但食物已经被打包好,和其他外卖订单放在一起;还有一次在一家咖啡店想用陶瓷杯,却被告知店里只有外带纸杯。
“当餐厅只把堂食当附加业务,他们就不会再经营那种让人聚在一起的空间。”Mintz说。
如今的多伦多,外卖已不再是权宜之计,而是餐饮业的主流模式。只是,对很多老板来说,这条路走得越久,利润越薄,氛围越淡——但没有退路。
你会为了支持一家喜欢的餐厅,特地去堂食吗?还是外卖的方便已经让你回不去了?



